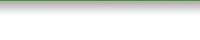电企跨界煤化工集体陷窘境
浏览数:6 | 日期:2014-4-26
3月底,中国华能、中国大唐、中国华电、中国国电、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、国投集团、神华集团等国内电力巨头齐聚一堂,但交流的却不是电力业务,而是各企业在煤化工发展规划、煤化工项目建设营运、煤化工业务结构及企业人才状况、煤化工工艺选择及技术储备等方面的情况。
在近些年国内煤化工热潮的带动下,这种跨行业搞煤化工的事不稀奇。那么,这些电力企业的煤化工业务开展得如何?是否一帆风顺呢?
“逼上梁山”发展煤化工
从多家电力企业了解到,电力企业搞煤化工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。2005年以来,我国电力行业的发展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。火电产能全面过剩,节能减排压力进一步加大,发电成本居高不下,行业面临全面亏损的困局。发展电力离不开煤炭,“拿煤”是电力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。而要拿煤矿,地方政府开出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按一定比例就地转化。于是,电力企业被“逼上梁山”发展煤化工。
多家电力企业的现身说法,印证了这一事实。
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煤炭部经济运营处副处长董建立介绍说,“我们公司是在2010年拿煤炭资源时被带进了煤化工领域。”2010年华电集团因为拿煤“被化工”了4个煤化工项目,当年就决策了煤制气、煤制乙二醇等项目,2011年又在陕西榆林上马了天然气制甲醇项目和煤制甲醇项目。天然气制甲醇项目效益不好,2011年天然气由每立方米1.11元涨到1.6元,项目成本增加了2亿多元,2013年亏了1.6亿元,今年预计亏得还要多。
中国国电集团煤化工部赵丽梅也承认,国电集团发展煤化工是迫不得已。2008年、2009年国电集团先后拿到200亿吨的煤矿,配套了6个煤化工项目,其中有的是在兼并煤矿的过程中带过来的。2012年,国电集团形成了6000万吨煤炭产能和6个煤化工项目,于是国电集团干脆成立了煤化工产业部,干起了煤化工。
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高新产业部煤化工处处长米文珍则表示,“我们发展煤化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为了掌握煤炭资源,按照地方政府的要求,我们必须进行煤炭的就地转化,且地方政府对转化的比例越来越高,原来是1∶0.5,现在要求1∶1了。”
大唐集团相关负责人也承认,他们拿到某地一个70亿吨储量的褐煤矿,先后上马了一个46万吨/年的煤制聚丙烯项目和一个40亿立方米/年的煤制天然气项目,项目总投资数百亿元。还有一个化肥项目虽为拿煤而建,但时至今日,项目建起来了,煤矿却没了下文。大唐也是典型的因煤资源而“被化工”的代表。
技术难题难以逾越
毋庸置疑,这些电力公司都是国内的行业巨头,搞发电肯定没的说,搞煤化工又如何呢?
中国华能集团煤炭部经济运营处副处长刘宇介绍说,华能集团在天津的IGCC项目中,气化炉采用华能自己开发的干粉气化技术,但从2013年运行一年的情况看,气化炉因煤质影响运行不稳定,尚在摸索和完善之中。华能集团在新疆的一个煤制气项目搞了4年多的技术论证,最担心的还是气化技术。
刘宇诉苦称,“我们担心的还有煤的问题。由于煤矿与煤化工项目同步开发,在煤化工项目的前期要把煤质搞清楚十分困难,煤在地下,采样有局限性,数据不一定具有代表性。块煤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,由于鲁奇气化炉专‘吃’块煤,且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,所以还不知道从开采到进炉,块煤还剩多大比例,剩下大量的粉煤又怎么办。”
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高新产业部煤化工处处长米文珍则称,“刚开始并不觉得搞煤化工多么复杂,但后来发现煤化工比电力复杂得多,搞煤化工在技术的先进性和管理难度上都比搞电力更难。不过大唐的示范项目让我们接受了一些教训,公司经常反复讨论比选方案。”
大唐作为五大发电集团最早进入煤化工领域的企业,在煤化工技术方面的感触尤为深刻。从大唐能源化工公司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,大唐的煤化工项目都遇到过技术瓶颈的制约。大唐内蒙古多伦煤化工项目自2006年开始建设以来,可谓命运多舛。由于当地煤质原因,气化技术掌握难度大,正式生产以来,气化炉时常“发脾气”,导致“气头”负荷一直偏低。大唐克旗煤制气项目一系列装置投运仅一个多月,就因煤质中不明化学成分等原因出现气化炉内壁严重磨损现象,项目被迫停产检修近2个月,最近才重新恢复生产。
中国国电集团煤化工部赵丽梅介绍说,国电集团煤化工项目出现的问题,主要表现在电力企业对煤化工项目认识不到位,往往容易以电力的思维看化工,结果忽视了一些致命的技术问题。
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煤炭部经济运营处副处长董建立则抱怨,电力企业搞煤化工心里都没底,找不到非常权威的机构建议。“因为各个化工设计院看法不一样,公说公有理、婆说婆有理,站在不同的角度,针对不同的技术说得都很好,让我们拿不定主意。”